我們很多人可能有這樣的經(jīng)歷��,和一些在國(guó)外工作機(jī)構(gòu)的人聊天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他們經(jīng)常會(huì)中英文混說��,但你能想到這件事同時(shí)也發(fā)生在一位85歲老人身上嗎�����?從簡(jiǎn)單的“It's a easy”到“program management”這樣的專業(yè)詞匯��,很自然的從他嘴里發(fā)出來����。感覺就像母語一般純熟。
原來�,王松年的英文得益于他的大學(xué)教育。1947年�����,17歲的少年考取了上海財(cái)經(jīng)大學(xué)的前身——國(guó)立上海商學(xué)院��。學(xué)校里用的教材全部是英文,教授的也是西方會(huì)計(jì)��。英語和會(huì)計(jì)的結(jié)合�����,使日后王松年選擇國(guó)際會(huì)計(jì)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�。他也沒有辜負(fù)這份令很多同輩人望塵莫及的語言優(yōu)勢(shì),在國(guó)際會(huì)計(jì)領(lǐng)域幾十年如一日地勤奮耕耘���,為師�,桃李滿天下����;為學(xué),碩果累累����。
幸運(yùn)的“會(huì)計(jì)初體驗(yàn)”
王松年1930年出生于一個(gè)很普通的平民家庭��。他的父親由于很小就父母雙亡����,8歲就從老家紹興來到上海學(xué)做生意���。憑著自己的努力,父親后來在一家私營(yíng)企業(yè)做到了經(jīng)理的位置��。他遺憾自己沒有讀書的機(jī)會(huì)���,所以盡管生活艱難��,仍盡可能支持孩子們讀書�����。
1947年��,17歲的王松年參加高考���。在考取國(guó)立上海商學(xué)院的同時(shí),他還考取了上海滬江大學(xué)����、同濟(jì)大學(xué)和復(fù)旦大學(xué)。王松年面臨著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�,他最終選擇了國(guó)立上海商學(xué)院。
“我們家?guī)讉€(gè)孩子都很努力��。我們首先就是要盡可能減少家里的負(fù)擔(dān)。所以希望考國(guó)立學(xué)校��,可以不要學(xué)費(fèi)�����,還有生活費(fèi)����。上商學(xué)院是為了容易找工作。當(dāng)時(shí)我們也沒有偉大的理想����,首先要吃飯。那時(shí)候我媽媽身體還很差�。”
進(jìn)了學(xué)校�,王松年才發(fā)現(xiàn)這個(gè)大學(xué)可不簡(jiǎn)單。老師們都是從國(guó)外回來的�,包括當(dāng)時(shí)在會(huì)計(jì)界已經(jīng)很知名的婁爾行先生。學(xué)校用的教材��,除了語文和三民主義�����,都是英文的��,內(nèi)容則是純正的西方會(huì)計(jì)�,而不是當(dāng)時(shí)國(guó)內(nèi)老式的收付記賬法會(huì)計(jì)。
1949年新中國(guó)成立后�����,盡管教學(xué)方面有所變化��,但也沒有一下子全變過來�。大學(xué)四年的學(xué)習(xí),為王松年日后從事國(guó)際會(huì)計(jì)的研究打下了堅(jiān)實(shí)的語言和專業(yè)基礎(chǔ)����。
1951年,王松年大學(xué)畢業(yè)��,很幸運(yùn)地留在了母校���。
“講起來���,我當(dāng)時(shí)還不是共產(chǎn)黨員,也不是青年團(tuán)員,我是書呆子�����。我留下來����,是因?yàn)槲页煽?jī)比較好,學(xué)校也需要一個(gè)學(xué)習(xí)好的人���。
大學(xué)畢業(yè)第二年�,王松年到中國(guó)人民大學(xué)攻讀工業(yè)會(huì)計(jì)方向的研究生��。當(dāng)時(shí)學(xué)的是前蘇聯(lián)的社會(huì)主義會(huì)計(jì)���。這和他大學(xué)學(xué)的西方會(huì)計(jì)顯然不太一樣�����。
“It's a easy���。為什么呢?因?yàn)槌思由像R克思主義的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在里面�,其他的都沒有什么。”鑒于在大學(xué)期間對(duì)西方會(huì)計(jì)的了解����,他認(rèn)為����,蘇聯(lián)的那套會(huì)計(jì),其實(shí)是從德國(guó)引進(jìn)的�����。但是��,當(dāng)時(shí)讀書的時(shí)候他并不敢公開這么說����。
“當(dāng)時(shí)是一邊倒的,美國(guó)的都是資本主義���,蘇聯(lián)是社會(huì)主義�����,西方的要批判的��,蘇聯(lián)的東西絕對(duì)是正確的�����。你講蘇聯(lián)一句不好��,就是犯法��。在這種政治形勢(shì)當(dāng)中��,我們?cè)趺锤抑v�,誰講就要批判他。現(xiàn)在都要講利潤(rùn)�����,很正常的���。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會(huì)計(jì)當(dāng)中����,它首先講一切要聽國(guó)家的統(tǒng)一計(jì)劃��,所以它分得很細(xì)���,一個(gè)蘿卜一個(gè)坑��?��!?/p>
1955年,王松年從人大研究生畢業(yè)����,回到了上財(cái)。他很幸運(yùn)地趕上了周恩來總理正在主管的落實(shí)知識(shí)分子政策�����。次年���,王松年就被評(píng)為講師���。
“這一輩人當(dāng)中,我是第一批評(píng)上講師的�����。那時(shí)評(píng)講師是挺不容易的���,不像現(xiàn)在��。以后就沒有這個(gè)好事了�。再評(píng)教授,已經(jīng)是幾十年之后的事情了����。”
被荒廢的“黃金時(shí)代”
建國(guó)初期的上海財(cái)經(jīng)學(xué)院���,會(huì)計(jì)教學(xué)科研從全國(guó)來說�,都是非常先進(jìn)的����。上財(cái)把蘇聯(lián)的一套東西結(jié)合中國(guó)的實(shí)際情況,出了一套教材����,就是由婁爾行主編,上海財(cái)政經(jīng)濟(jì)出版社1957-1958年陸續(xù)出版的《工業(yè)會(huì)計(jì)核算》����,當(dāng)時(shí)被成為“三分冊(cè)”,在會(huì)計(jì)學(xué)界產(chǎn)生了很大的影響���。會(huì)計(jì)學(xué)泰斗楊紀(jì)琬主編的《中國(guó)現(xiàn)代會(huì)計(jì)手冊(cè)》高度評(píng)價(jià)這套書�����,“是在學(xué)習(xí)蘇聯(lián)會(huì)計(jì)的基礎(chǔ)上結(jié)合我國(guó)實(shí)踐的中國(guó)化教材�,至今仍有一定參考價(jià)值?���!?/p>
從人大學(xué)成歸來的王松年���,也滿腔熱情地投身其中�����。但這種“激情燃燒的歲月”并沒有持續(xù)多久���,1958年受運(yùn)動(dòng)影響,上財(cái)關(guān)門�,教師隊(duì)伍四分五裂,王松年“流落”到了社科院�。
“一方面也教教書,但主要工作是管學(xué)生�。我做班主任�����,會(huì)計(jì)學(xué)生都是我一個(gè)人管���。和學(xué)生同吃同住同勞動(dòng),到農(nóng)村去�,到工廠去?���!?/p>
1961年,王松年再次面臨“分配”�。他沒有能回去新成立的上財(cái),而是“受到重用”�����,被分到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研究室��?�!罢窝芯渴?���,搞政治的�����,和會(huì)計(jì)全不搭界�?��!?/p>
文革開始后���,王松年也受到組織審查?!暗谝唬覜]有家庭問題�����,第二����,我本身聽黨的話���,沒有講過反動(dòng)話����。但是,從此我學(xué)到一點(diǎn)�,就是講話要小心,就是通常講的����,要夾緊尾巴做人。不應(yīng)該我講的話不去講����,就算有不同的看法,也盡可能少發(fā)表我個(gè)人的意見�。”
王松年的研究方向也受此影響�。“所以我搞什么呢�����?搞國(guó)際的東西�����,矛盾少���,而且��,我外文可以��,我就利用我的優(yōu)勢(shì)�。”
1978年�����,48歲的王松年回到了上財(cái)�。距離1958年關(guān)門,已經(jīng)過去了整整20年���。一個(gè)學(xué)者的“黃金時(shí)代”就這樣被荒廢了����。
“大器晚成”的國(guó)際會(huì)計(jì)大家
1978年上海財(cái)經(jīng)學(xué)院復(fù)校后����,和國(guó)外合作辦班的事業(yè)開始起步��。1981年3月�,為方便國(guó)際合作聯(lián)系,上財(cái)設(shè)立上海國(guó)際經(jīng)濟(jì)管理學(xué)院。1982年4月��,在國(guó)際經(jīng)濟(jì)管理學(xué)院內(nèi)設(shè)立培訓(xùn)中心��,王松年被任命為中心主任���,兼管外事組和語言培訓(xùn)等工作�。
培訓(xùn)中心負(fù)責(zé)的培訓(xùn)項(xiàng)目中���,最重要的是世界銀行在國(guó)內(nèi)辦的貸款項(xiàng)目培訓(xùn)��。
“世界銀行貸款給你���,都是要收回的。那時(shí)因?yàn)槲覀冎袊?guó)大量需要世行貸款����,所以你要培訓(xùn),要讓很多人懂��。培訓(xùn)有兩種班��,一個(gè)是高級(jí)班��,到美國(guó)華盛頓特區(qū)去學(xué)習(xí),就是到世界銀行本部去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�;第二個(gè)是中級(jí)班�����,是相當(dāng)于處一級(jí)的�,這個(gè)是我管?�!?/p>
1984年����,王松年成為上海財(cái)經(jīng)學(xué)院的副校長(zhǎng),分管教學(xué)和外事�。“教學(xué)從夜大學(xué)管起��,一直到博士生����,都是我管的��;所有外事的都是我管的?!?/p>
從1984年到1991年擔(dān)任上海財(cái)大副校長(zhǎng)(注:1985年,上海財(cái)經(jīng)學(xué)院更名為上海財(cái)經(jīng)大學(xué))的這段歲月�,王松年無論是在會(huì)計(jì)教學(xué)方面,還是在科研方面�����,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��。
1987年8月��,我國(guó)第一部用英文撰寫�,系統(tǒng)闡述我國(guó)會(huì)計(jì)審計(jì)的歷史、現(xiàn)狀��、制度�、理論和展望的學(xué)術(shù)專著《Accounting and auditing in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》(中文譯名:《中國(guó)的會(huì)計(jì)和審計(jì)》)在美國(guó)出版。這本書的中方主編是婁爾行和王松年��。他還參與撰寫了《中國(guó)預(yù)算會(huì)計(jì)》(英文稿)的論文����,于1990年由國(guó)際貨幣基金組織出版。
鑒于國(guó)際會(huì)計(jì)人才缺乏的現(xiàn)狀���,1989年�����,由王松年主導(dǎo)�����,上海財(cái)大和上海外國(guó)語大學(xué)聯(lián)合開辦國(guó)際會(huì)計(jì)班��。
“學(xué)生前兩年在外國(guó)語大學(xué)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,后面兩年到上財(cái)。所有外語課都用外國(guó)人教�����,專業(yè)課全部都是我們上財(cái)上���。第一年教會(huì)計(jì)��,教材都是英文版的�����。學(xué)生買不起教材��,我就用亞洲基金會(huì)提供的舊書���。全部上課都要講英文。教師也都是我定的���,包括湯云為���、張為國(guó)等?�!?/p>
1991年�����,王松年退休��,和上外的合作辦學(xué)也由于種種原因而終止�。盡管只是短短的幾年合作辦學(xué),但卻為業(yè)界培養(yǎng)了不少既懂外語又懂會(huì)計(jì)的雙料人才����,而這種合作辦學(xué)的嘗試也為我國(guó)的會(huì)計(jì)人才培養(yǎng)開創(chuàng)了一種全新的模式�����。
在上海財(cái)大期間��,王松年曾經(jīng)多次出國(guó)���,對(duì)于國(guó)外會(huì)計(jì)的實(shí)踐和理論頗有研究。
1978年�����,剛剛回到上海財(cái)大�����,王松年就被教育部派往斯洛文尼亞(前南斯拉夫的一個(gè)加盟共和國(guó)�,1991年6月25日獲得獨(dú)立)。由于出色的英文�,王松年被介紹到聯(lián)合國(guó)下屬的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Enterprises。在這個(gè)機(jī)構(gòu)里��,王松年接觸到了大量的英文資料�,也得到了很多到參觀其他國(guó)家的機(jī)會(huì)。
這次的出國(guó)經(jīng)歷���,使王松年對(duì)南斯拉夫的會(huì)計(jì)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����。“南斯拉夫有一個(gè)優(yōu)點(diǎn)�,就是講經(jīng)濟(jì)理論����。我們?cè)趪?guó)內(nèi)念書的時(shí)候,是講馬克思主義��,是工人創(chuàng)造勞動(dòng)����,其他人,包括知識(shí)分子都靠邊站�����,你是吃人家的����。但南斯拉夫講�,勞動(dòng)是相互交換的���,你工人的小孩要進(jìn)小學(xué)吧�,那小學(xué)老師的勞動(dòng)就同你工人的勞動(dòng)相互交換���。就是說�,工人創(chuàng)造價(jià)值���,知識(shí)分子也創(chuàng)造價(jià)值�?����!?/p>
南斯拉夫的經(jīng)濟(jì)理論讓王松年“很開竅”��。他經(jīng)過深入研究���,發(fā)表了多篇關(guān)于南斯拉夫會(huì)計(jì)��,以及評(píng)價(jià)南斯拉夫基層組織經(jīng)濟(jì)效益指標(biāo)體系的論文。這是中國(guó)學(xué)術(shù)界對(duì)于南斯拉夫會(huì)計(jì)的首次系統(tǒng)論述�。
1991年,退休后的王松年來到了美國(guó)��,擔(dān)任科羅拉多州州立大學(xué)商學(xué)院的客座教授��,講授會(huì)計(jì)學(xué)和國(guó)際會(huì)計(jì)�?����!拔矣X得這一年多的時(shí)間收獲不小����,但是就是年齡大一點(diǎn),精力也不夠了�����。如果年紀(jì)輕一點(diǎn)��,回來對(duì)國(guó)家的貢獻(xiàn)可能更大?��!?/p>
為人師表的“老實(shí)人”
王松年1959年入黨���。但是,他其實(shí)是一個(gè)對(duì)政治無感的人��。他不是沒有從政的機(jī)會(huì)���。1961年���,31歲的王松年被分到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研究室。
文化大革命期間���,王松年差點(diǎn)被調(diào)去做人民日?qǐng)?bào)駐外記者���。“當(dāng)時(shí)通過組織部已經(jīng)正式任命下來了��。我后來沒有去���。我想我是搞會(huì)計(jì)的�����,不是記者出身���。那時(shí)四人幫還當(dāng)權(quán)����,這么做風(fēng)險(xiǎn)是很大的���?���!?/p>
粉碎四人幫以后���,組織又要調(diào)王松年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?�!拔抑v我不搞這個(gè)���,因?yàn)檎块T我待過了����。我不是這個(gè)料。我想我還是吃本科���、研究生會(huì)計(jì)的這個(gè)飯���。我也有興趣�。我不要求去做什么官�����,有教師做就好了�����?�!?/p>
他認(rèn)定自己只是個(gè)教書的料�����,在教書這件事上就格外投入和認(rèn)真�����。
他的學(xué)生彭玉龍一直記得一件事:有一晚上王松年臨時(shí)給碩士研究生代課���,一共要講3個(gè)小時(shí),到了最后�,學(xué)生們看出老師講課有些艱難。后來才知道���,他為了不耽誤大家的時(shí)間��,沒有吃晚飯����。那時(shí)候��,他已經(jīng)是70歲的高齡�����。
彭玉龍還記得曾經(jīng)和恩師一起編寫一本國(guó)際會(huì)計(jì)的教材��,恩師告誡他:編教材不是寫論文�����,寫論文容許犯錯(cuò)誤����,但教材不允許。教材要求你寫出的內(nèi)容是目前公認(rèn)的�,并且不能有歧義。因?yàn)橐槐窘滩膶?duì)學(xué)生的影響太大了�����,特別是對(duì)那些辨別能力還有限的本科生而言����。
他帶博士帶了將近20年,但一共只帶了30來個(gè)博士生�。
“我從來沒有想擴(kuò)大招生規(guī)模。我一個(gè)人一屆最多兩三個(gè)學(xué)生����。我哪里有精力帶那么多學(xué)生。有時(shí)候給學(xué)生看論文���,我是一個(gè)字一個(gè)字地看����、改。首先大的框架定下來�,最后定稿的時(shí)候有的學(xué)生的論文還是有很多問題,要花很大精力改的����。后來我年紀(jì)一點(diǎn)點(diǎn)大起來了,精力也更少一點(diǎn)了�����。所以�,我不要那么多學(xué)生,太多我就給人家了�����?�!?/p>
對(duì)于自己85年的人生���,王松年的評(píng)價(jià)很平實(shí)低調(diào):“就三個(gè)字�����,普通人�,一個(gè)普通教師�����?��!?/p>
注:本文根據(jù)2013年9月23日王松年老師的口述記錄整理���。初稿成自2015年5月4日,二稿于2016年3月18日��。2017年11月18日經(jīng)王松年老師夫人沈漪蘭女士審核定稿��。
來源:中國(guó)會(huì)計(jì)視野
 客服服務(wù)
客服服務(wù)
 下載APP
下載APP
 歡迎來到會(huì)計(jì)網(wǎng)登錄
歡迎來到會(huì)計(jì)網(wǎng)登錄 登錄/注冊(cè)?? 后您將獲得
登錄/注冊(cè)?? 后您將獲得 海量學(xué)習(xí)資料
海量學(xué)習(xí)資料
 完整考試題庫
完整考試題庫
 老師急速答疑
立即登陸
老師急速答疑
立即登陸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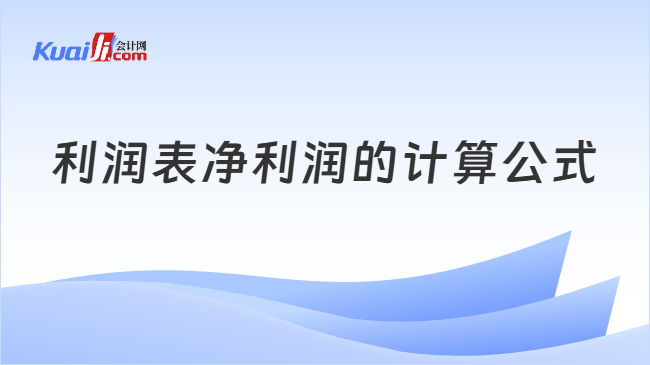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滬公網(wǎng)安備
31010902002985號(hào)
滬公網(wǎng)安備
31010902002985號(hào) 上海市互聯(lián)網(wǎng)舉報(bào)中心
上海市互聯(lián)網(wǎng)舉報(bào)中心
 中央網(wǎng)信辦舉報(bào)中心
中央網(wǎng)信辦舉報(bào)中心
